 Laurent Ponsot
Laurent Ponsot
Laurent Ponsot或许是个集各种极端于一身的人物。他掌持了30年的Domaine Ponsot早已跻身勃艮第精英之列。酒庄在种植,酿造,尤其是包装运输方面的高科技创新可谓引领潮流,包括Ponsot特制防伪酒瓶和酒标,瓶塞,智能酒箱和栈板运输温度感测器等等。然而酒庄在葡萄园管理和葡萄酒陈酿方面却秉承了一些最古老甚至早被遗忘的做法。在其颠覆传统条条框框的表象背后,特立独行的Laurent Ponsot是否在向传统之精髓回归?
Mei:您是勃艮第最晚收的酒庄之一。您是如何确定最佳采收日的?
LP:我确定采收日的方法其实同葡萄本身毫无关系。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Morey-Saint-Denis百合花开的那一天,根据葡萄园周边各类花草虫鸟活动轨迹所提供的指示符,再结合春分时刻的月相,我计算出当年的采收起始日。其实这种老法已延续了两千年,其精准度有史为证。我们的祖先比自以为是的现代人更懂得在大自然中寻找暗示,因为花草鱼虫比我们人类有着敏锐数倍的直觉。我从1983年执掌酒庄以来就一直以这个方法来测算采收日,并从未因采收而品尝过一颗葡萄或做过一个实验室分析。30年来几乎没有差错。(Mei注:酒庄众多酒款皆以虫鸟来命名,例如:苍头燕雀,画眉,云雀,熊蜂,黑鸟,蝉,等等,似乎同庄主对大自然的迷恋不无相关)

Mei:真的毫无例外?难道没有不可预料的自然因素吗?
LP:唯一的例外是2003:热浪与干旱的严重程度和延续时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决定比预计提早采收,但还是比大部分人晚很多-例如,Clos de la Roche是9月14日采收的,比不少酒农晚了近一个月。上面提到的这种方法唯一无法预测的是葡萄园中疾病的袭击与蔓延。例如1994年,灰霉菌几乎吞没我们所有产区的葡萄,酒庄所有酒款一律降级,这个年份没有Domaine Ponsot的特级园。我认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判断失误。对于菌类疾病,我们从不盲目使用化学喷洒剂或因此恐慌地提前采收。采收前夕和期间,我们在葡萄园中反复进行极度严格的人工筛选,及时剔除受损葡萄,防止疾病扩散。而这个过程的人工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如果说,完美的成熟度必须以产量损失作为代价,我们从未犹豫过。20年来,酒庄的平均单产量保持在每公顷2500公升以下。我们的品质正来源于此。
Mei:酒庄能做出如此的选择也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后盾,不是吗?一些经济能力较差的酒庄将无力承受如此惨重的产量损失?
LP:当我从父亲那里接手,酒庄其实处在欠债状态,经济条件非常差。今天我们的酒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并以更高的价格销售,这一切都起源于当初义无反顾品质至上的承诺。

Mei:您如何看待生物动力法?
LP:生物动力的精髓是对土地和大自然的尊重,而这一点Ponsot家族的祖先其实早就在奉行了。我们一直以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耕种,而非为提高产量而强迫施作。今天一些时兴的潮流其实是重新挖掘早已相传几千年的农法与理念,并为之贴上新的时髦标签。Domaine Ponsot不隶属任何流派,但我们在“自然”之路上走的很远。例如,自1983年以来,我就从未使用过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使得我们的葡萄园处在极佳的健康状态。但面对像黄化病(Flavescene Dorée)这样的疾病,化学制剂的干预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不会受某些教条束缚而对葡萄园视死不救!生物动力的有些做法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它具有宗派性质。
Mei:有些所谓的顶级年份,风土特征似乎被年份特征所覆盖,您怎么看?
LP:这个我很同意。有一次在美国演讲,我做了一个有趣的表格,虽然不很精准,但表达了我的大致想法。以Domaine Ponsot的酒为例,从1999至2010年份,年份特征和风土表达的比例大致如下:

Mei:您对2004年的感受使我惊讶, 我个人觉得2004的年份特征似乎还是很明显的。Domaine Ponsot的2004是否有所谓的“瓢虫气息”?
LP:绝对没有!2004是个灾难重重的年份,冰雹加上各种菌类疾病泛滥。但2004年采收季得益于灿烂的“印度之夏”,Domaine Ponsot作为勃艮第历来最晚采收的酒庄,等到了最后也采到了成熟度很高的葡萄,再加上极度苛刻的筛选,我们的2004绝没有成熟度低下所带来的青涩之味。但正如人会经历迷茫困惑的青春期一般,2004在装瓶后很长一段时间表现相当封闭甚至令人费解,但最近这段时间似乎开始回归正道。1995年份也有着类似的成长轨迹,我坚信这个杰出的年份终将自我呈现。为了能够持续享受葡萄酒带给我们的幸福和愉悦,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她的脾气,骄纵与缺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有耐心,事事求快的世界中,潮流驱使我们追逐即刻速成的快感。我们传统的葡萄酒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所欣赏,只有经历了漫长且完整的青少年期的酝酿,人们方能领略到她成熟细致的风采。

Mei:您是否根据年份特征调整陈酿手段?
LP:是的。没有一个年份我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浸泡时间长短,萃取强弱,木桶醇化时间等等每年都有变化。例如,伟大的1990年份经历了近3年的木桶陈年,而我们目前正在为2012年份装瓶,这意味着28个月的陈酿期。
Mei:那您是否根据产区风土调整陈酿技法?
LP:绝对不!我不会因产区差异而改变我的做法-酒庄目前有21个不同酒款,从大区Bourgogne一直到特级园,都以相同的方式陈酿,旨在忠实透明的呈现每片风土之独特个性。如果说风土是乐谱的话,我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乐队指挥,而所有其他因素-种植和陈酿的手段,设备,人员-都是由我支配的演奏家们。我的目标不是表现自己,而是最忠实的再现原作之美。伟大的酒之所以触动我们的心灵,正因为她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而这种感动我们的生命力只可能源自风土,而非陈酿期间的技术介入和修正。

Mei:Ponsot风格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您在酿造过程中保持了那些传统,又进行了哪些革新呢?
LP:所谓Ponsot风格并不存在,我的理念是在自然面前隐身,让风土得到最纯粹的表达。或许这种”无风格”最终反变成了一种风格。我认为勃艮第传统的精髓在于尊重自然,尽少的人为操纵和干预。1985年我负责酒庄酿造不久,决定停止人工澄清,我父亲当时认为我将因此摧毁酒庄的酒。从某种意义上,我是回归到我祖父那辈人的理念。我热爱历史,却痛恨打着传统的旗号延续祖辈错误愚昧的做法。你知道吗?第戎芥末之所以成为本地一大特产正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利用了葡萄酒醋 - 那个时代酿造业频繁失误的副产品(笑)。现代酿酒术最大的进步其实是卫生水准的飞越。那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年代的酿造环境可想而知。要酿出一桶好酒,至少需要使用两桶的水(来保证至高的卫生水准)。我不拒绝21世纪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只要这能服务于我最大程度尊重和再现风土的初衷。例如,酒庄购入的一台捷豹跨式拖拉机,配备低压轮胎,可以在35%坡面上保持水平作业,它对土壤的踩压力甚至小于“传统”的马力耕田。又如,酒庄近几年引入发酵桶电脑温控系统,也旨在提高葡萄酒在风土表达上的精准度。但另一方面,酒庄至今仍在沿用一个1940年代的垂直压汁机。
Mei:说起酿造过程,您能否就Domaine Ponsot一些标志性的做法详细聊聊。比如发酵的温控问题
LP:很久以来,我对发酵时的温度是抱着相当放任的态度的,当然红酒酿造期间最高温度基本控制在36度以下。然而自然中有些东西是无法解释的。我记得1985这个炎热的年份,由于当时没有温控设备,采来的葡萄在12小时内就开始发酵,3天内发酵就结束了,根本没有经过今天流行的所谓“冷浸泡”。1985年Clos de la Roche发酵时的温度最高达到40摄氏度。当年Robert Park在其装瓶后打了90分,但五六年前他重品了这款酒,将打分更新到100分。
Mei:(大笑)这样的酒没有过高的挥发酸吗?
LP:所有勃艮第伟大的酒都是含很高挥发酸接近缺陷边缘的酒,你下次注意去观察一下!我说所有!!分析数据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我最近品尝了祖父酿的1949年份Clos de la Roche, 酒精度是15%,酸度极低,但是这款酒依然呈现出深红的色泽,活力非凡!
Mei:您反对全梗酿造,不是吗?
LP:你说到传统,去梗才是勃艮第的传统,我这里还有一个中世纪修道士使用的原始去梗机可以为证。全梗酿造是博若莱产区的传统,罗马人时代就已有记录。而对于勃艮第黑皮诺来说,梗味则会掩盖其纯净细腻的芬芳并带来清苦的气息。支持者都会告诉你他们用的梗是成熟的,但葡萄梗其实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成熟的。
Mei:您在酿造和木桶陈年过程中几乎不添加二氧化硫,是否可以把您的酒称做“自然酒”?
LP:我不想隶属任何派系,不受任何教条束缚,我的规则是没有规则!确实,我们在整个陈酿过程和装瓶前都几乎不加二氧化硫,因为没有必要。我们最大限度上不去干扰葡萄酒本身安静漫长的醇化过程。木桶中的酒总是加的满满的,没有任何被氧化的机会。装瓶前仅换一次桶,并且在惰性气体充分保护下进行。而使用旧木桶的一大好处是其比新桶细小很多的气孔使得氧化过程变得更缓慢。我们最新的装瓶流水线也确保对氧气侵入的最大掌控-所有作业都在20摄氏度恒温惰性气体中进行,连清洗酒瓶的水也经过净化并除氯。当然,我们对陈酿期间葡萄酒的状态进行严格的跟踪分析和监控,并保留必要时刻采取特殊措施的自由和可能,比如2003年份我们就加了二氧化硫,因为桶里的挥发酸含量已经达到危险边缘。
Mei:您忌讳新木桶的使用,为什么呢?
LP: 因为旧木桶才是勃艮第真正的传统,正如新木桶是波尔多的传统一样。我喝过Domaine Leflaive表现非凡的Batard-Montrachet 1972年份,是现庄主Anne-Claude之父所酿,当时他没有使用一点新木桶。而我家的Corton Charlemagne也同样没有一丁点新木桶。我从勃艮第最顶尖的白酒庄购买二手木桶,例如Domaine des Comtes Lafon就是其中之一。
Mei:有些人对您的做法似乎不以为然,有些酒评人认为您的酒品质风格不够稳定。
LP:要么去试图取悦所有的人,要么努力酿出伟大的酒。二者不可能兼顾。“不稳定”对我来说更像是恭维之语,标准化才是勃艮第的噩梦。

Mei:您对酒商酒是怎么看的?酒商酒也能达到顶级酒农酒的水准吗?
LP:我痛恨所有陈腐的偏见。认为酒商酒肯定不好是很荒谬的。直到80年代早期,勃艮第85%以上的酒都是由酒商酿造的。Domaine Ponsot实质上就是一个酒商,我们家族既拥有自己的田产(Mei注:Ponsot家族其实从1930年代起就是勃艮第最早实行domaine bottling的酒农),同时也收购葡萄来酿造和陈年。1989年起我们注册了PONSOT商标。从我父亲的时代起,酒庄就开始同Remy, Mercier等家族签订了田产长期租赁合同(Métayage),例如我们的Chambertin, Griottes-Chambertin和Clos Saint Denis特级园皆非出自Ponsot家族田产。而从2002年起,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启动,我把它叫做Joint Venture。Domaine Ponsot同勃艮第一些最优秀的酒农(他们中某些人的声望要求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共同照料葡萄园,采收时一半葡萄由我庄买下。虽然法律上这些葡萄酿出的酒隶属酒商酒,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葡萄园管理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并且同合作伙伴并肩工作,确保我们的理念和指标得到精准的贯彻与执行。今天酒庄的Chambertin Clos de Bèze, Charmes-Chambertin, Clos Vougeot, Corton以及Corton Charlemagne特级园都是这种性质的酒。它们的酒标同Domaine Ponsot其它的酒没有区别。
Mei :您对外来的投资报怎样的态度?这是否会威胁到勃艮第精神的世代延续?30年后的勃艮第将变成怎样?
LP:当某些勃艮第人在酒标上印上黑皮诺几个字的那一刻,勃艮第的灵魂就已经迷失了。真正的勃艮第不应该是在酿造黑皮诺,而应力图表达其丰富独特的风土。我认为外来投资是大势所趋,30年后的勃艮第肯定将不再由勃艮第人所拥有!但为什么要忧心忡忡呢?或许会有很多来自亚洲的投资人。我对亚洲带着无比的好感,我的妻子和儿媳都是亚洲人。亚洲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精致的文化底蕴或许反能为勃艮第带来福音!
Mei:中国大陆不乏您的崇拜者。您的酒目前在中国大陆是怎样销售的?
LP:其实我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出口到中国大陆。但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合作在2007年终止了。我目前准备委任酒庄的台湾进口商兼顾中国大陆业务。我计划明年重访中国。
![]()


![]()
![]()
罕见一手视频,深入揭秘顶尖勃艮第白酒庄压榨现场 — 2020年份采收跟踪报道之伯恩丘
洪梅 Mei Hong![]()
触目惊心!勃艮第1976年以来最惨重旱灾 — 2020年份采收跟踪报道之首篇
洪梅 Mei Hong![]()
DRC 庄主 Aubert de Villaine 一对一深度访谈录
洪梅 Mei Hong![]()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 专访 - 来自巴赫的灵感
洪梅 Mei Hong![]()
Laurent Ponsot 专访 — 所有伟大的酒,都是接近缺陷边缘的酒
洪梅 Mei Hong![]()
私访 Domaine des Comtes Lafon - 深度探讨提早氧化问题
洪梅 Mei Hong![]()
Chateau de Pommard — Michael Baum:在勃艮第拥有酒庄是一种奢华
洪梅 Mei Hong![]()
Emmanuel Rouget 专访 - 关于Henri Jayer的私密回忆
洪梅 Mei Hong![]()
卓越还是平庸?2016 年勃艮第金丘深度年份报道
洪梅 Mei Hong![]()
2016 年历史性春霜 — 4月27日黑色星期三,勃艮第35年来最大梦魇
洪梅 Mei Hong![]()
牟超:风起于青萍之末,入藏三年后的至暗时刻
牟超![]()
Pierre Morey专访 - 好年份的风土特征,反需更长时间显现
洪梅 Mei Hong![]()
LVMH 收购 Clos des Lambrays 引强烈震荡
洪梅 Mei Hong


 Laurent Ponsot
Laurent Ponsot
Laurent Ponsot或许是个集各种极端于一身的人物。他掌持了30年的Domaine Ponsot早已跻身勃艮第精英之列。酒庄在种植,酿造,尤其是包装运输方面的高科技创新可谓引领潮流,包括Ponsot特制防伪酒瓶和酒标,瓶塞,智能酒箱和栈板运输温度感测器等等。然而酒庄在葡萄园管理和葡萄酒陈酿方面却秉承了一些最古老甚至早被遗忘的做法。在其颠覆传统条条框框的表象背后,特立独行的Laurent Ponsot是否在向传统之精髓回归?
Mei:您是勃艮第最晚收的酒庄之一。您是如何确定最佳采收日的?
LP:我确定采收日的方法其实同葡萄本身毫无关系。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Morey-Saint-Denis百合花开的那一天,根据葡萄园周边各类花草虫鸟活动轨迹所提供的指示符,再结合春分时刻的月相,我计算出当年的采收起始日。其实这种老法已延续了两千年,其精准度有史为证。我们的祖先比自以为是的现代人更懂得在大自然中寻找暗示,因为花草鱼虫比我们人类有着敏锐数倍的直觉。我从1983年执掌酒庄以来就一直以这个方法来测算采收日,并从未因采收而品尝过一颗葡萄或做过一个实验室分析。30年来几乎没有差错。(Mei注:酒庄众多酒款皆以虫鸟来命名,例如:苍头燕雀,画眉,云雀,熊蜂,黑鸟,蝉,等等,似乎同庄主对大自然的迷恋不无相关)

Mei:真的毫无例外?难道没有不可预料的自然因素吗?
LP:唯一的例外是2003:热浪与干旱的严重程度和延续时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决定比预计提早采收,但还是比大部分人晚很多-例如,Clos de la Roche是9月14日采收的,比不少酒农晚了近一个月。上面提到的这种方法唯一无法预测的是葡萄园中疾病的袭击与蔓延。例如1994年,灰霉菌几乎吞没我们所有产区的葡萄,酒庄所有酒款一律降级,这个年份没有Domaine Ponsot的特级园。我认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判断失误。对于菌类疾病,我们从不盲目使用化学喷洒剂或因此恐慌地提前采收。采收前夕和期间,我们在葡萄园中反复进行极度严格的人工筛选,及时剔除受损葡萄,防止疾病扩散。而这个过程的人工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如果说,完美的成熟度必须以产量损失作为代价,我们从未犹豫过。20年来,酒庄的平均单产量保持在每公顷2500公升以下。我们的品质正来源于此。
Mei:酒庄能做出如此的选择也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后盾,不是吗?一些经济能力较差的酒庄将无力承受如此惨重的产量损失?
LP:当我从父亲那里接手,酒庄其实处在欠债状态,经济条件非常差。今天我们的酒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并以更高的价格销售,这一切都起源于当初义无反顾品质至上的承诺。

Mei:您如何看待生物动力法?
LP:生物动力的精髓是对土地和大自然的尊重,而这一点Ponsot家族的祖先其实早就在奉行了。我们一直以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耕种,而非为提高产量而强迫施作。今天一些时兴的潮流其实是重新挖掘早已相传几千年的农法与理念,并为之贴上新的时髦标签。Domaine Ponsot不隶属任何流派,但我们在“自然”之路上走的很远。例如,自1983年以来,我就从未使用过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使得我们的葡萄园处在极佳的健康状态。但面对像黄化病(Flavescene Dorée)这样的疾病,化学制剂的干预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不会受某些教条束缚而对葡萄园视死不救!生物动力的有些做法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它具有宗派性质。
Mei:有些所谓的顶级年份,风土特征似乎被年份特征所覆盖,您怎么看?
LP:这个我很同意。有一次在美国演讲,我做了一个有趣的表格,虽然不很精准,但表达了我的大致想法。以Domaine Ponsot的酒为例,从1999至2010年份,年份特征和风土表达的比例大致如下:

Mei:您对2004年的感受使我惊讶, 我个人觉得2004的年份特征似乎还是很明显的。Domaine Ponsot的2004是否有所谓的“瓢虫气息”?
LP:绝对没有!2004是个灾难重重的年份,冰雹加上各种菌类疾病泛滥。但2004年采收季得益于灿烂的“印度之夏”,Domaine Ponsot作为勃艮第历来最晚采收的酒庄,等到了最后也采到了成熟度很高的葡萄,再加上极度苛刻的筛选,我们的2004绝没有成熟度低下所带来的青涩之味。但正如人会经历迷茫困惑的青春期一般,2004在装瓶后很长一段时间表现相当封闭甚至令人费解,但最近这段时间似乎开始回归正道。1995年份也有着类似的成长轨迹,我坚信这个杰出的年份终将自我呈现。为了能够持续享受葡萄酒带给我们的幸福和愉悦,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她的脾气,骄纵与缺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有耐心,事事求快的世界中,潮流驱使我们追逐即刻速成的快感。我们传统的葡萄酒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所欣赏,只有经历了漫长且完整的青少年期的酝酿,人们方能领略到她成熟细致的风采。

Mei:您是否根据年份特征调整陈酿手段?
LP:是的。没有一个年份我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浸泡时间长短,萃取强弱,木桶醇化时间等等每年都有变化。例如,伟大的1990年份经历了近3年的木桶陈年,而我们目前正在为2012年份装瓶,这意味着28个月的陈酿期。
Mei:那您是否根据产区风土调整陈酿技法?
LP:绝对不!我不会因产区差异而改变我的做法-酒庄目前有21个不同酒款,从大区Bourgogne一直到特级园,都以相同的方式陈酿,旨在忠实透明的呈现每片风土之独特个性。如果说风土是乐谱的话,我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乐队指挥,而所有其他因素-种植和陈酿的手段,设备,人员-都是由我支配的演奏家们。我的目标不是表现自己,而是最忠实的再现原作之美。伟大的酒之所以触动我们的心灵,正因为她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而这种感动我们的生命力只可能源自风土,而非陈酿期间的技术介入和修正。

Mei:Ponsot风格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您在酿造过程中保持了那些传统,又进行了哪些革新呢?
LP:所谓Ponsot风格并不存在,我的理念是在自然面前隐身,让风土得到最纯粹的表达。或许这种”无风格”最终反变成了一种风格。我认为勃艮第传统的精髓在于尊重自然,尽少的人为操纵和干预。1985年我负责酒庄酿造不久,决定停止人工澄清,我父亲当时认为我将因此摧毁酒庄的酒。从某种意义上,我是回归到我祖父那辈人的理念。我热爱历史,却痛恨打着传统的旗号延续祖辈错误愚昧的做法。你知道吗?第戎芥末之所以成为本地一大特产正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利用了葡萄酒醋 - 那个时代酿造业频繁失误的副产品(笑)。现代酿酒术最大的进步其实是卫生水准的飞越。那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年代的酿造环境可想而知。要酿出一桶好酒,至少需要使用两桶的水(来保证至高的卫生水准)。我不拒绝21世纪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只要这能服务于我最大程度尊重和再现风土的初衷。例如,酒庄购入的一台捷豹跨式拖拉机,配备低压轮胎,可以在35%坡面上保持水平作业,它对土壤的踩压力甚至小于“传统”的马力耕田。又如,酒庄近几年引入发酵桶电脑温控系统,也旨在提高葡萄酒在风土表达上的精准度。但另一方面,酒庄至今仍在沿用一个1940年代的垂直压汁机。
Mei:说起酿造过程,您能否就Domaine Ponsot一些标志性的做法详细聊聊。比如发酵的温控问题
LP:很久以来,我对发酵时的温度是抱着相当放任的态度的,当然红酒酿造期间最高温度基本控制在36度以下。然而自然中有些东西是无法解释的。我记得1985这个炎热的年份,由于当时没有温控设备,采来的葡萄在12小时内就开始发酵,3天内发酵就结束了,根本没有经过今天流行的所谓“冷浸泡”。1985年Clos de la Roche发酵时的温度最高达到40摄氏度。当年Robert Park在其装瓶后打了90分,但五六年前他重品了这款酒,将打分更新到100分。
Mei:(大笑)这样的酒没有过高的挥发酸吗?
LP:所有勃艮第伟大的酒都是含很高挥发酸接近缺陷边缘的酒,你下次注意去观察一下!我说所有!!分析数据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我最近品尝了祖父酿的1949年份Clos de la Roche, 酒精度是15%,酸度极低,但是这款酒依然呈现出深红的色泽,活力非凡!
Mei:您反对全梗酿造,不是吗?
LP:你说到传统,去梗才是勃艮第的传统,我这里还有一个中世纪修道士使用的原始去梗机可以为证。全梗酿造是博若莱产区的传统,罗马人时代就已有记录。而对于勃艮第黑皮诺来说,梗味则会掩盖其纯净细腻的芬芳并带来清苦的气息。支持者都会告诉你他们用的梗是成熟的,但葡萄梗其实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成熟的。
Mei:您在酿造和木桶陈年过程中几乎不添加二氧化硫,是否可以把您的酒称做“自然酒”?
LP:我不想隶属任何派系,不受任何教条束缚,我的规则是没有规则!确实,我们在整个陈酿过程和装瓶前都几乎不加二氧化硫,因为没有必要。我们最大限度上不去干扰葡萄酒本身安静漫长的醇化过程。木桶中的酒总是加的满满的,没有任何被氧化的机会。装瓶前仅换一次桶,并且在惰性气体充分保护下进行。而使用旧木桶的一大好处是其比新桶细小很多的气孔使得氧化过程变得更缓慢。我们最新的装瓶流水线也确保对氧气侵入的最大掌控-所有作业都在20摄氏度恒温惰性气体中进行,连清洗酒瓶的水也经过净化并除氯。当然,我们对陈酿期间葡萄酒的状态进行严格的跟踪分析和监控,并保留必要时刻采取特殊措施的自由和可能,比如2003年份我们就加了二氧化硫,因为桶里的挥发酸含量已经达到危险边缘。
Mei:您忌讳新木桶的使用,为什么呢?
LP: 因为旧木桶才是勃艮第真正的传统,正如新木桶是波尔多的传统一样。我喝过Domaine Leflaive表现非凡的Batard-Montrachet 1972年份,是现庄主Anne-Claude之父所酿,当时他没有使用一点新木桶。而我家的Corton Charlemagne也同样没有一丁点新木桶。我从勃艮第最顶尖的白酒庄购买二手木桶,例如Domaine des Comtes Lafon就是其中之一。
Mei:有些人对您的做法似乎不以为然,有些酒评人认为您的酒品质风格不够稳定。
LP:要么去试图取悦所有的人,要么努力酿出伟大的酒。二者不可能兼顾。“不稳定”对我来说更像是恭维之语,标准化才是勃艮第的噩梦。

Mei:您对酒商酒是怎么看的?酒商酒也能达到顶级酒农酒的水准吗?
LP:我痛恨所有陈腐的偏见。认为酒商酒肯定不好是很荒谬的。直到80年代早期,勃艮第85%以上的酒都是由酒商酿造的。Domaine Ponsot实质上就是一个酒商,我们家族既拥有自己的田产(Mei注:Ponsot家族其实从1930年代起就是勃艮第最早实行domaine bottling的酒农),同时也收购葡萄来酿造和陈年。1989年起我们注册了PONSOT商标。从我父亲的时代起,酒庄就开始同Remy, Mercier等家族签订了田产长期租赁合同(Métayage),例如我们的Chambertin, Griottes-Chambertin和Clos Saint Denis特级园皆非出自Ponsot家族田产。而从2002年起,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启动,我把它叫做Joint Venture。Domaine Ponsot同勃艮第一些最优秀的酒农(他们中某些人的声望要求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共同照料葡萄园,采收时一半葡萄由我庄买下。虽然法律上这些葡萄酿出的酒隶属酒商酒,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葡萄园管理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并且同合作伙伴并肩工作,确保我们的理念和指标得到精准的贯彻与执行。今天酒庄的Chambertin Clos de Bèze, Charmes-Chambertin, Clos Vougeot, Corton以及Corton Charlemagne特级园都是这种性质的酒。它们的酒标同Domaine Ponsot其它的酒没有区别。
Mei :您对外来的投资报怎样的态度?这是否会威胁到勃艮第精神的世代延续?30年后的勃艮第将变成怎样?
LP:当某些勃艮第人在酒标上印上黑皮诺几个字的那一刻,勃艮第的灵魂就已经迷失了。真正的勃艮第不应该是在酿造黑皮诺,而应力图表达其丰富独特的风土。我认为外来投资是大势所趋,30年后的勃艮第肯定将不再由勃艮第人所拥有!但为什么要忧心忡忡呢?或许会有很多来自亚洲的投资人。我对亚洲带着无比的好感,我的妻子和儿媳都是亚洲人。亚洲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精致的文化底蕴或许反能为勃艮第带来福音!
Mei:中国大陆不乏您的崇拜者。您的酒目前在中国大陆是怎样销售的?
LP:其实我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出口到中国大陆。但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合作在2007年终止了。我目前准备委任酒庄的台湾进口商兼顾中国大陆业务。我计划明年重访中国。
![]()

更 多 文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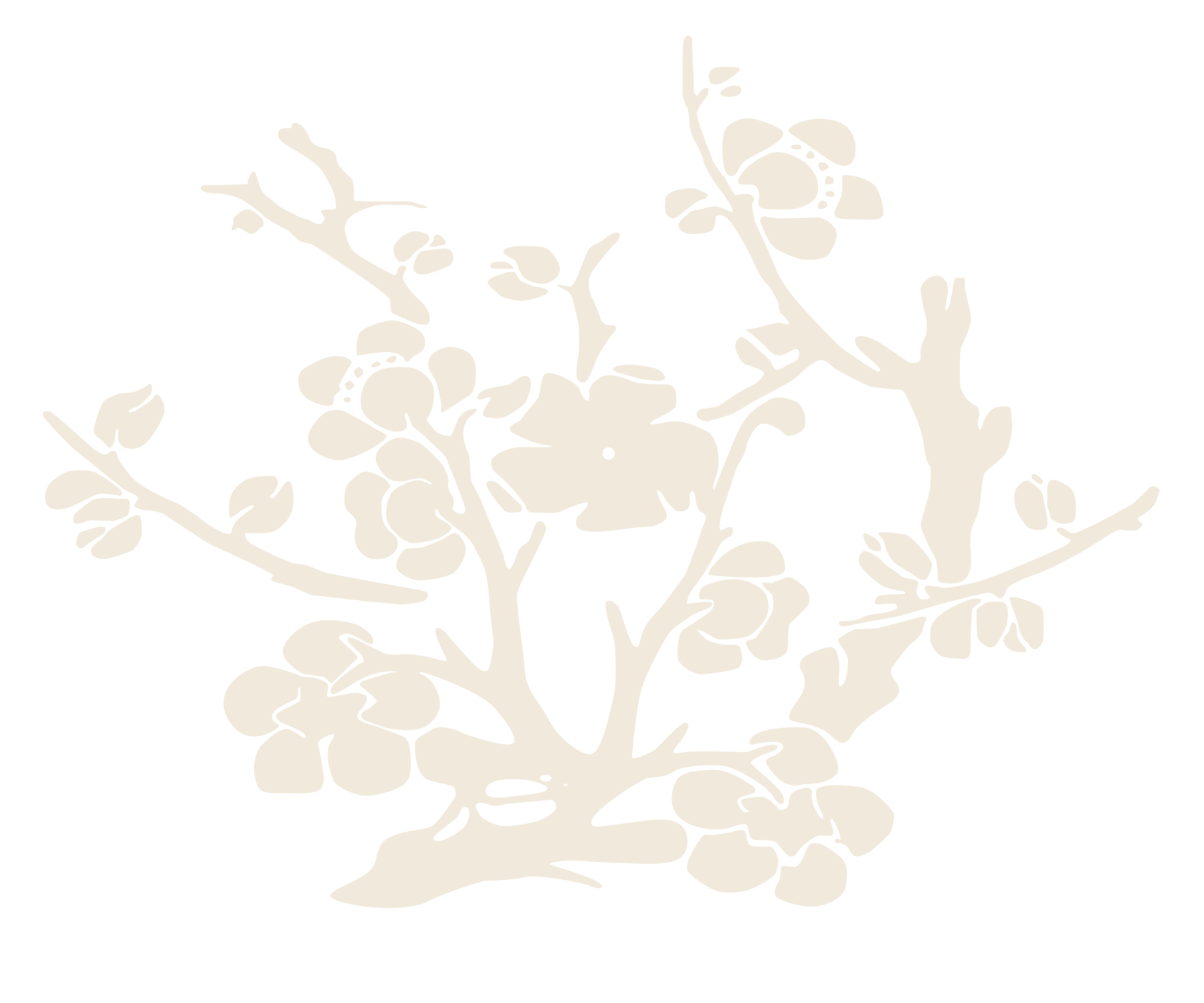
梅 专 栏


![]()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深深的怀念是什么?对话JFM, 共品2019年份
Mei Hong![]()
罕见一手视频,深入揭秘顶尖勃艮第白酒庄压榨现场 — 2020年份采收跟踪报道之伯恩丘
洪梅 Mei Hong![]()
触目惊心!勃艮第1976年以来最惨重旱灾 — 2020年份采收跟踪报道之首篇
洪梅 Mei Hong![]()
DRC 庄主 Aubert de Villaine 一对一深度访谈录
洪梅 Mei Hong![]()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 专访 - 来自巴赫的灵感
洪梅 Mei Hong![]()
Laurent Ponsot 专访 — 所有伟大的酒,都是接近缺陷边缘的酒
洪梅 Mei Hong![]()
私访 Domaine des Comtes Lafon - 深度探讨提早氧化问题
洪梅 Mei Hong![]()
Chateau de Pommard — Michael Baum:在勃艮第拥有酒庄是一种奢华
洪梅 Mei Hong
5 Place de L'Europe, 21630 Pommard, Côte d'Or, France
contact@mhclimatsselections.com
5 Place de L'Europe, 21630 Pommard, Côte d'Or, France
contact@mhclimatsselections.com
本网站所有照片,除非特别标注,皆由 Mei Hong 本人拍摄。版权归属作者,未经允许请勿转发。
© E.U.R.L MH Climats Sélections![]()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8535号 沪ICP备2020026059号-1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8535号 沪ICP备2020026059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