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专栏 > 文章内容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同Georges Roumier和Comte de Vogüe常被并称为Chambolle-Musigny最伟大的演绎者。而Mugnier酒特有的清透深邃更另不少收藏家对其情有独钟。JFM本人之低调内敛以及对外界的疏远更频添其神秘色彩。在圣诞前宁静阴冷的日子里,我有幸两次拜访这位当代勃艮第最受膜拜的酒农,在近4小时的私密交谈和品鉴中,从其智慧与个性魅力中得到无数灵感。
Wine vs Art
Mei: 您作为石油工程师的早期训练影响到您作为酒农到思维运作方式吗?
JFM: 当然有,但事实上工程师和酒农的思维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工程师解决问题时力图简单客观,酿酒则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是主观的,无法由有限几个参数或公式来决定。
Mei: 酿酒更像是创造艺术作品,不是吗?
JFM: 从欣赏者角度,确实如此:伟大的葡萄酒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能激发灵魂深处的感动。但酿酒同艺术品的创造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艺术品是人类精神之结晶,伟大的葡萄酒却是大自然的杰作。作为酒农,我并没有发明创造什么,仅仅尽所能完美透明的将这个杰作呈现出来。

Mei: 在这个把名庄酿酒师捧做明星的世界,您的这个说法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新奇的,尤其在新世界。
JFM: 才华横溢的酿酒师比比皆是,风土却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至少对于勃艮第而言,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理念。
Mei: Allen Meadows说您的酒风有“禅”一般的感觉。您力图在风土之前隐身,而您的个性烙印即是没有烙印。但即便是有着相同理念的酿酒师,对同一片风土还是会有迥异的诠释。比如您同Christophe Roumier, 你们的Bonnes Mares, Les Amoureuses, Musigny喝起来都截然不同。
每个酒农其实都是一张过滤网…
JFM: 因为每个酒农其实都是一张过滤网,而我同Roumier是两张不同的过滤网而已(狡诘的眨眼)! 如果说风土的潜能在葡萄园中是百分之一百的话,在酿酒和陈年的过程中,一部分风土的信息必将失掉-被过滤,被修改,被模糊,甚至被摧毁。再优秀的酒农也无法创造出新的,葡萄原先不具备的价值;他的才华在于,从采收直至最后装瓶,通过每一步深思熟虑的选择,尽其所能减小风土信息之损失,从而最大程度上忠实还原风土的本来面目。
Mei: 就像一个乐队指挥,忠实的演绎乐谱一般。。。
“too much piano playing”...
- Glenn Goude
JFM: 我喜欢酿酒同音乐的比较(微笑)。每每同杰出的音乐家交谈,他们总强调:“乐谱,乐谱,还是乐谱”!优秀的演奏者应该力图真实完整的再现原作真髓,而不是在此之上强加其个人色彩-这同风土至上的酿酒理念是一脉相通的。Glenn Goude并非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巴赫演绎者,但他的某些评论却令我深有同感。在1981年重录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后,回顾其1955年版本时,他说,早先的版本有“too much piano playing”...
Mei: 正如今天很多的酒有“too much wine-making”!
JFM: 正是!
Mei: 您表面上的“无为”,其实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索。。。
JFM: 至少在酿酒房,我每年的改进都旨在尽可能减少人为介入,将现有步奏简单化。来我酒庄的实习生往往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在我的酿酒房和酒窖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但这种“极简主义”风格在葡萄园管理上却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葡萄园的情况完全相反。我坚信,葡萄藤天然的发展倾向同人类所希望产出优质葡萄的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正因如此,葡萄藤需要被引导,被强制,被胁迫,方能按照人类的意愿发展。葡萄园的管理需要非常多的人工介入,众多工作的本质在于同天然趋势做“斗争”,包括剪枝,去芽,去叶,绿色收割等等。葡萄树必须被迫挣扎方能产出富有风土表达力的好酒。
“极简主义”风格在葡萄园管理上
却是根本行不通的
Mei: 我很好奇,假设,某年由您的团队按贵庄的方式来料理和采收Domaine Roumier的葡萄园,例如爱侣园,由您来陈酿,将会出现怎样风格的酒呢?
JFM: 有一点是肯定的,酿出来的酒同我自己以及Roumier的爱侣园都将有区别。虽然同是爱侣园, 我家和Roumier家地块的特性有诸多区别:不仅是不同的树种,藤龄,根系,剪枝方式等等,一块地的特性是几十年,上百年劳作的结晶,是它整个历史的写照,不是短期管理和酿酒房的后期加工所能改变的。而即使Roumier本人来我家酒窖酿他自家的葡萄,他还是不会酿出相同的Roumier。从葡萄园到最后装瓶,这中间的每一动作每一细节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种植篇
Mei: 自1985年掌持酒庄以来,您在种植管理上采取了哪些您认为对葡萄品质产生巨大影响的措施呢?
JFM: 对于葡萄园而言,首要因素其实是树种和砧木的选择。可惜在这方面我没有太多作为,我接管酒庄以来并没有大面积重新栽种。另一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土壤之维护。要产出具有风土表达力的葡萄酒,充满生命力的土壤是根本前提。这意味着保持包括根系,矿物质,菌类,天然酵母,动植物在内的整条生化链之完整,使得葡萄树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酒庄自1986起停止使用工业化肥,1990年起彻底摈弃除草剂,1995起告别杀虫剂。每年二月至八月初,定期进行浅层土壤松土除草(binage)的工作。
Mei: 然而酒庄并非完全有机化,而是隶属“合理抗争”(Lutte Raisonnée)的类别,不是吗?
JFM: 我同有机酒农最根本的区别,或许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对霜霉病(mildiou)的治理方法上。“无药不毒”乃是大自然之法则。抗争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将无酒可酿。而每种抗争方式都各有各的副作用,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使用有机契约所允许的硫酸铜,还是放弃“有机”使用合成杀菌剂(synthetic fungicides)?硫酸铜有剧毒,且很难化解,会慢慢在土壤中累积。从长远看,我认为使用硫酸铜的恶果将大于化学杀菌剂。“有机”是种标签,推行一整套行为标准,它迫使你做出死板,甚至夸张可笑的决定。

“我同有机酒农最根本的区别,或许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对霜霉病(mildiou)的治理方法上。。。从长远看,我认为使用硫酸铜的恶果将大于化学杀菌剂”
Mei: 回到种植方面的重要举措,除了上面提到的土壤维护,还有其他哪些呢?
JFM: 种植方面另一重要改变,是在2005以后逐步采用一种特殊的剪枝(Taille)方式。30年以下的“年轻”葡萄藤全部改用Cordon de Royat。老藤还是用Guyot剪枝法,但同过去只留4到6个芽眼的做法不同,我们决定保留10至12个芽眼的长枝条。每年到了四月下旬,则进行抹芽工作,去除一半贅芽,使得剩下的枝梢拥有更宽松的空间,更有效的利用光照。
Mei: 这样做之后的收益是否很明显?
JFM: 我观测到,在过去十年中我家葡萄的成熟期提前,葡萄树具备更强悍的抗白粉病和灰霉病能力。这种剪枝方式的缺点是技术要求高,费钱费时费力。如果处理不当,抹芽工作未在短时间内完成,贅芽将发展成幼梢,去除将对葡萄树带来伤害,使之疲惫。
长枝修剪法是Mugnier葡萄园中的“秘密”之一
Mei: 酒庄是否施行摘叶(éffeuillage)及绿色收割呢?
JFM: 很少去叶,主要是在花季开始前一段时间有选择性的摘除一些重叠的叶子,主要目的是预防白粉病。我庄最后一次绿色收割是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天然产量都极为低下,老天替我们完成了绿色收割。历史上曾出现过既产量丰沛又高质的年份,例如1999和2009。遗憾的是过去几年-2015年份除外-出产高品质的葡萄酒都必须以牺牲产量作为代价,别无选择。

Mei: 让我们来谈谈采收时机的问题。在Chambolle-Musigny村内,即便顶级酒庄之间,采收日亦会相差甚远。例如,Domaine du Comte de Vogue总是村里最早采收的,贵庄有时在其之后一周才开始。您到底是怎样决定采收日的呢?
JFM: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酒庄葡萄园的状况。即便同一产区,各家葡萄树状态的不同就必然导致采收时机的不同。在90年代,我家往往是村内最晚采收的酒庄,但在过去几年中却成了偏早采收的酒庄之一。这同我们的葡萄成熟期加快和提前有很大关系,我本人的决策原则其实并未有太多改变。对于黑皮诺而言,葡萄皮的酚类物质成熟度是我决定采收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只能通过亲自品尝葡萄提样来完成。我会咀嚼葡萄皮:一开始它是青涩无味的,单宁突兀干苦;慢慢的,葡萄皮中单宁会变圆润且富有香气。有些年份,即便潜在酒精度已经颇高,酸度下滑,还是必须耐心等待酚类物质充分成熟才能采摘。
各酒庄葡萄园状况之不同是导致其采收时机有差异的重要原因
Mei: 如果酒精度过高酸度下滑,您难道没有过熟的担忧吗?
JFM: 我丝毫不担心酒精度过高的问题,有些年份如2009年,我们有些酒款的酒精度超过14%,在2015年份,特级园的酒精度也都接近这个水平。
陈酿篇
Mei: 现在能否较详细的聊一下您陈酿方面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从采收开始。贵庄拒绝使用筛选台,这是为什么呢?
JFM: 所有的筛选工作都在田间完成,这是最有效也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我们采收季50个员工中45个在葡萄园采收,只有5个留在酒庄。筛选台对于排除不成熟的小个青涩颗粒有效,但对于勃艮第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灰霉菌。如果腐烂受损颗粒不在葡萄园中及时剔除,所渗出的带菌汁液在运输中将很快感染其它葡萄。我个人痛恨筛选台的工作方式。葡萄园中的筛选是种自然明智的工作,聚光灯下的筛选台却更像是个工厂,是可恶愚蠢低效的。我庄具备一个震动台,足已起到自动甩除水滴,昆虫和小颗粒未熟葡萄的作用。我们给予采收工足够的时间认真有效的完成他们的工作,人工筛选台在我看来是多余的。
如果腐烂受损颗粒不在葡萄园中及时剔除,所渗出的带菌汁液在运输中将很快感染其它葡萄
Mei: 贵庄的葡萄都是100%去梗发酵的,您从未尝试过带梗酿造吗?
JFM: 我确实尝试过!事实上,我庄1985至1993年份出品的酒都或多或少带梗。但在品尝比较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这种做法。我发现,全梗酿造的酒陈年后确实相当复杂诱人,但在年轻时却略带青涩之气,缺乏果味和圆润的口感,往往显得单薄冷峻。去梗之后,这些缺陷明显得到修正,并且我相信陈年潜力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全梗酿造的酒陈年后确实相当复杂诱人,但在年轻时却略带青涩之气,缺乏果味和圆润的口感,往往显得单薄冷峻
Mei: 您使用发酵前冷浸泡萃取吗?
JFM: 如果采收期间天气过热,我会将葡萄温度降到14-15度,但并不人为维持低温以延缓发酵,所以应该说,我并不施行所谓的“冷浸泡”。我同时使用不锈钢和橡木桶两种不同容器:木桶中的葡萄2-3天后发酵就自然开始,不锈钢中的则通常需要一周的时间。通过柔缓的去梗动作,我们尽量保持葡萄颗粒的完整无缺,这对放慢和拉长发酵过程以及萃取皮中复杂精致的香气至关重要。也正因此,我发酵期间几乎从不踩皮(pigeage),萃取是通过偶尔淋皮(remontage)非常柔和的进行。
通过柔缓的去梗动作,我们尽量保持葡萄颗粒的完整无缺,这对放慢和拉长发酵过程以及萃取皮中复杂精致的香气至关重要
Mei: 那您是在什么时刻开始踩皮动作呢?您是否对发酵施行温度控制?
JFM: 我对温度是控制的,但发酵期间温度上升的相当缓慢。整个浸皮发酵(cuvaison)持续长达18-20天,温度却到最后才抵达顶峰-可以高达38-40摄氏度。此刻,果汁中糖份已基本全部转换成酒精,最后的踩皮动作将促使葡萄颗粒中尚存的糖分最后释放,从而延长发酵时间。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持续一周之长。之后我们会榨汁,自然澄清24小时后入桶。自流汁(vin de goutte)和压榨汁(vin de presse)分开陈年,但后者最终往往还是混入前者。

Mei: 您在添加二氧化硫上的做法是怎样的?
JFM: 我对二氧化硫的添加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的最低量。通常仅在酒精发酵开始前和乳酸菌发酵完成之后极少量添加。除此之外整个漫长的18-20个月的木桶醇化期间,我基本上不添加一点二氧化硫。
Mei: 你是否通过装瓶时注入少量二氧化碳以弥补二氧化硫之低含量,增进酒的抗氧能力?
JFM: 二氧化碳是不能取代二氧化硫功能的。况且,二氧化碳含量必须保持在品鉴无法感知的限度以内,也就是每升600mg以下。我庄二氧化碳的含量通常在每升350-550mg之间,而在酸度偏高的年份则会相应少加,因为二氧化碳有锐化酸度的作用。
我对二氧化硫的添加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的最低量
Mei: 您对时下流行的“自然酒”(Mei注:完全不添加二氧化硫的酒)怎么看?
JFM: 我并不在意尝试这些酒。上次我喝了一款2008年份的“自然酒”,感觉像1959年份的。“自然酒”中酿酒技法的痕迹通常覆盖了风土的表达。几乎所有的“自然酒”都具有同样的,陈酿技法所带来的香气,人们很难分辨出它的风土来源。我觉得作为酒农,我们必须对最终消费者负责,而不应仅仅为了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哲学理念而酿酒。
“自然酒”中酿酒技法的痕迹通常
覆盖了风土的表达

Mei: 酒庄现在用新桶的比例是多少?对橡木的出处是否有特殊要求?
JFM: 不论年份产区,都在15-20%左右。我们同François Frères以及Remond橡木厂合作。我们当然选用最优质的橡木桶。但介于我们新木比例之低,橡木的特性对酒的品质及风格影响极小。
Mei: 贵庄的酒是否出现过瓶塞污染(TCA)的问题?您是如何控制木塞的品质的?
JFM: 我们在2004后替换了木塞供应商,并始终保持与三个不同供应商同时合作。首先,我们对生产商施加了一套严格的规格流程章法。到货之后,我们会首先在实验室中进行TCA含量测试。之后,进行第二道测试:将任选的100个瓶塞在纯净水中浸泡24小时,之后品尝木塞浸泡过的水。这道测试旨在检测木塞中除了TCA之外的其他异味,例如霉味等。目前我庄的木塞感染率一般控制在1%以下。
Mei: 那些不幸遇到1%TCA污染的客户是否能将酒退回呢?
JFM: 客户可以将瓶塞寄回酒庄,我们会对之进行实验室测试。如果经鉴定确实瓶塞污染,我们会提供替换服务。

Mei: 酒庄是否有考虑使用防伪设计?
JFM: 康帝庄庄主Aubert de Villaine曾同我商讨过共同协调抗伪的计划。我个人对此不是太感兴趣。我不想把我家的酒标设计成类似银行钞票。伪造品的存在正好提醒收藏家,让他们意识到从官方渠道购买葡萄酒的重要性。否则后果自负。
Mei: 很多收藏家朋友询问,酒庄的Clos de la Maréchale为何酒标上没有注明Monopole?
JFM: 对我而言,Monopole (独占园)同品质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我不觉得有把它印在酒标上的必要。其实,如果您注意酒标上最下面一行小字:“Seul Propriétaire au Chateau de Chambolle-Musigny”- 已经注明独占园性质。
Mei: 在我们过去的交谈中您曾提过,陈酿方面,你对所有葡萄园都一视同仁。不论出处,都以同样的方式发酵和醇化,您这样做背后的逻辑和理念是什么呢?
JFM: 是的,为了最大程度上透明地表达风土特征,我对所有产区都严格采用完全一致的方式陈酿,包括浸皮的时间,萃取之强弱,发酵温度,新木桶比例,装瓶时间等等,手法上都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信奉风土至上的理念,就不应该人为的强迫一款酒同它的天然倾向背道而驰。我们不应力图矫正某片风土的特征,弥补它个性上所谓的不足。我认为只有在陈酿中秉持绝对中性的原则,方能凸显每片风土的本色。
“如果我们信奉风土至上的理念,就不应该人为的强迫一款酒同它的天然倾向背道而驰。我们不应力图矫正某片风土的特征,弥补它个性上所谓的不足”
Mei: 那对于不同年份呢?
JFM: 我绝不根据不同年份调整我的陈酿手段。每个年份都有它的独特性,这也正是它有趣之处。比如,有些年份颜色深邃,有些则非常浅,天然使成,何必强迫每个年份都给出同样的颜色?在我刚接手酒庄时,曾经试图根据风土和年份调整技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例如,在寒冷的年份,成熟度偏低,单宁少颜色淡。你会说,这样的年份需要更多的人工介入,更强劲的萃取,方能弥补年份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你亦可理论,寒冷年份的单宁偏于青涩干苦,必须格外柔和萃取方可避免不熟的单宁渗入酒汁。又如,在新桶比例上,你会说,村级的酒缺乏天然的单宁,多些新木桶正好可以增强其结构感,而特级园本来就富含包括单宁在内的天然多酚物质,故而不需太多的新木桶带来更多的单宁;然而,反向推理也是可行的:村级酒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内涵和力度,故而木桶使用必须含蓄以免盖过酒本身的个性表达,而强大的特级园则能承受更高比例的新木桶。一开始,我陷入矛盾中,就决定不分风土年份一律以同样方式酿造陈年。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哲学。

Mei: 是否可以说,您对大自然是完全信赖的?
JFM: 是的,在陈酿上,我并不给风土和年份划分高低等级:对于每片风土,每个年份,我们必须尊重它特有的和谐。这些年,我愈发深信,大自然有着她自身的和谐。如果我们试图扭曲她,那么,我们做的越多,破坏天然和谐的风险就越大。你无法在酿酒房内重建平衡:现代陈酿技术无法将原先不平衡的变得平衡。大自然本身的和谐有时是人类知识无法充分解释的。在无知中我们必须承认,自然总是最完美的。
“大自然有着她自身的和谐。。你无法在酿酒房内重建平衡-现代陈酿技术无法将原先不平衡的变得平衡”
Mei: 聊到年份问题,最让您倾心的是那个年份?
JFM: 我不在意告诉你,但我的回答很可能造成误导。因为我是从酿酒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这同爱好者收藏家的角度可能很不同。对我而言,我最爱的年份往往是那些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最令我骄傲的年份。这往往是一些带来惊喜结果的艰难年份。
Mei: 例如?
JFM: 例如2013就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我31年的酿酒生涯里,几乎从未经历过老一辈人所描述的像60,7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年份。2013年,我曾一度对自己说,或许,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份。然而,结果却充满惊喜。2013年份丰满深邃,它的圆润肥厚对于这样一个寒冷艰难的年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刚入桶不久,它的酸度似乎有些突出,现在却完美无痕的融入酒体。或许2013并非易饮诱人,讨喜大众的年份,但却个性鲜明,并具备在我看来比2012和2014都更强的陈年潜力。当然这些都是就我们庄的酒而言。
“2013年份丰满深邃。。。具备比2012和2014都更强的陈年潜力”
Mei: 除了2013,还有那些年份给您带来了惊喜?
JFM: 2010,2008,2004都是这样的年份。2010现已成为公认的杰出年份,但在采收的时刻,对于这个年份的潜质却众说纷纭。2004对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一年,我们收回了Clos de la Maréchale, 酒庄的产量翻了3倍多。我雇佣了新的7人团队,扩建了酒窖(拥有四层场地空间),添加了新的酿酒设备。2004是个极为艰难的年份,葡萄园间的工作充满挑战。
Mei: 不少人认为2004年份特有的青涩气息同那年有很多瓢虫有关。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JFM: 2004年份确实有很多瓢虫,需要在筛选时剔除。但这仅仅是因素之一。很多青涩其实同葡萄成熟度欠缺有关。这个年份的单产量必须控制在很低,否则绝对产不出好酒。Clos de la Maréchale在2004年经历了绿色收割,一半以上的葡萄被去除!2004成为令我自豪的高品质年份。
2004年份的很多青涩其实同葡萄成熟度欠缺有关。这个年份的单产量必须控制在很低,否则绝对产不出好酒

Mei: 媒体对于创造“伟大”年份也功不可没,例如最新的2015年份。您对这个年份怎么看?
JFM: 2015是一个极其极其伟大的年份(降低音量)。但我们对此不应该过多宣扬!
Mei: 2015年份是否有酸度偏低的担忧?
JFM: 现在下定论或许过早,但我对2015黑皮诺缺乏酸度的说法不敢苟同。确实,采收来的葡萄总酸度偏低,但其中苹果酸的比例和钾(发酵期间会中合葡萄汁和酒汁中的酸)的含量都非常低 - 这意味着2015将是个酸度非常稳定的年份。
Mei: 许多收藏家会关心贵庄的酒何时能进入适饮期?
JFM: 我们庄的酒,一个“小年”的村级陈年潜力是10到20年;如果是杰出年份,则需40-50年方可抵达巅峰。例如Chambolle-Musigny Village 1990年份现在仍很年轻,远未达到它的顶峰。而对于一级园和特级园,陈年潜力几乎是无限的。
一个“小年”的村级陈年潜力是10到20年;如果是杰出年份,则需40-50年方可抵达巅峰
Mei: 这么说,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享受到鼎盛时期的杰出年份和杰出风土? 像2005这样昂贵的年份,或许需要很久方能打开。。。
JFM: 我总是同客户强调,伟大年份和伟大的酒从来都不是愉悦感的同义词。一款酒之伟大存在于它仍未兑现的未来,而非衡量今日享受之尺度。此刻能给我们带来最大乐趣的往往并非这些酒。作为收藏家,只购买所谓的伟大年份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伟大年份和伟大的酒
从来都不是愉悦感的同义词“
Mei: 从酿酒技术的角度和哲学角度,请问您对一款伟大的酒的定义是什么?
JFM: 从技术角度,一款伟大的酒的真正标志是其回甘长度(longueur),因为这是据我所知唯一无法用现代技术手段在酿酒房中创造出来的“优点”。其他因素,例如,酸度,甜度,香气,木桶,浓郁度等等,都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来调整甚至伪装。从哲学角度,一款伟大的酒之真髓隐藏于它此刻尚未呈现的那部分。你手中这杯年轻的酒,你现在所能感受到的它的一切,往往仅是其全部内涵的冰山一角,它的秘密存在于其演变中无法揣测的未来。一款伟大的酒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慢慢揭示其神秘的面纱下的真实面容。
从技术角度,一款伟大的酒的真正标志是其回甘长度(longueur);从哲学角度,一款伟大的酒之真髓隐藏于它此刻尚未呈现的那部分。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
Jacques-Frédéric Mugnier同Georges Roumier和Comte de Vogüe常被并称为Chambolle-Musigny最伟大的演绎者。而Mugnier酒特有的清透深邃更另不少收藏家对其情有独钟。JFM本人之低调内敛以及对外界的疏远更频添其神秘色彩。在圣诞前宁静阴冷的日子里,我有幸两次拜访这位当代勃艮第最受膜拜的酒农,在近4小时的私密交谈和品鉴中,从其智慧与个性魅力中得到无数灵感。
Wine vs Art
Mei: 您作为石油工程师的早期训练影响到您作为酒农到思维运作方式吗?
JFM: 当然有,但事实上工程师和酒农的思维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工程师解决问题时力图简单客观,酿酒则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是主观的,无法由有限几个参数或公式来决定。
Mei: 酿酒更像是创造艺术作品,不是吗?
JFM: 从欣赏者角度,确实如此:伟大的葡萄酒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能激发灵魂深处的感动。但酿酒同艺术品的创造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艺术品是人类精神之结晶,伟大的葡萄酒却是大自然的杰作。作为酒农,我并没有发明创造什么,仅仅尽所能完美透明的将这个杰作呈现出来。

Mei: 在这个把名庄酿酒师捧做明星的世界,您的这个说法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新奇的,尤其在新世界。
JFM: 才华横溢的酿酒师比比皆是,风土却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至少对于勃艮第而言,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理念。
Mei: Allen Meadows说您的酒风有“禅”一般的感觉。您力图在风土之前隐身,而您的个性烙印即是没有烙印。但即便是有着相同理念的酿酒师,对同一片风土还是会有迥异的诠释。比如您同Christophe Roumier, 你们的Bonnes Mares, Les Amoureuses, Musigny喝起来都截然不同。
每个酒农其实都是一张过滤网…
JFM: 因为每个酒农其实都是一张过滤网,而我同Roumier是两张不同的过滤网而已(狡诘的眨眼)! 如果说风土的潜能在葡萄园中是百分之一百的话,在酿酒和陈年的过程中,一部分风土的信息必将失掉-被过滤,被修改,被模糊,甚至被摧毁。再优秀的酒农也无法创造出新的,葡萄原先不具备的价值;他的才华在于,从采收直至最后装瓶,通过每一步深思熟虑的选择,尽其所能减小风土信息之损失,从而最大程度上忠实还原风土的本来面目。
Mei: 就像一个乐队指挥,忠实的演绎乐谱一般。。。
“too much piano playing”...
- Glenn Goude
JFM: 我喜欢酿酒同音乐的比较(微笑)。每每同杰出的音乐家交谈,他们总强调:“乐谱,乐谱,还是乐谱”!优秀的演奏者应该力图真实完整的再现原作真髓,而不是在此之上强加其个人色彩-这同风土至上的酿酒理念是一脉相通的。Glenn Goude并非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巴赫演绎者,但他的某些评论却令我深有同感。在1981年重录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后,回顾其1955年版本时,他说,早先的版本有“too much piano playing”...
Mei: 正如今天很多的酒有“too much wine-making”!
JFM: 正是!
Mei: 您表面上的“无为”,其实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索。。。
JFM: 至少在酿酒房,我每年的改进都旨在尽可能减少人为介入,将现有步奏简单化。来我酒庄的实习生往往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在我的酿酒房和酒窖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但这种“极简主义”风格在葡萄园管理上却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葡萄园的情况完全相反。我坚信,葡萄藤天然的发展倾向同人类所希望产出优质葡萄的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正因如此,葡萄藤需要被引导,被强制,被胁迫,方能按照人类的意愿发展。葡萄园的管理需要非常多的人工介入,众多工作的本质在于同天然趋势做“斗争”,包括剪枝,去芽,去叶,绿色收割等等。葡萄树必须被迫挣扎方能产出富有风土表达力的好酒。
“极简主义”风格在葡萄园管理上
却是根本行不通的
Mei: 我很好奇,假设,某年由您的团队按贵庄的方式来料理和采收Domaine Roumier的葡萄园,例如爱侣园,由您来陈酿,将会出现怎样风格的酒呢?
JFM: 有一点是肯定的,酿出来的酒同我自己以及Roumier的爱侣园都将有区别。虽然同是爱侣园, 我家和Roumier家地块的特性有诸多区别:不仅是不同的树种,藤龄,根系,剪枝方式等等,一块地的特性是几十年,上百年劳作的结晶,是它整个历史的写照,不是短期管理和酿酒房的后期加工所能改变的。而即使Roumier本人来我家酒窖酿他自家的葡萄,他还是不会酿出相同的Roumier。从葡萄园到最后装瓶,这中间的每一动作每一细节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种植篇
Mei: 自1985年掌持酒庄以来,您在种植管理上采取了哪些您认为对葡萄品质产生巨大影响的措施呢?
JFM: 对于葡萄园而言,首要因素其实是树种和砧木的选择。可惜在这方面我没有太多作为,我接管酒庄以来并没有大面积重新栽种。另一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土壤之维护。要产出具有风土表达力的葡萄酒,充满生命力的土壤是根本前提。这意味着保持包括根系,矿物质,菌类,天然酵母,动植物在内的整条生化链之完整,使得葡萄树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酒庄自1986起停止使用工业化肥,1990年起彻底摈弃除草剂,1995起告别杀虫剂。每年二月至八月初,定期进行浅层土壤松土除草(binage)的工作。
Mei: 然而酒庄并非完全有机化,而是隶属“合理抗争”(Lutte Raisonnée)的类别,不是吗?
JFM: 我同有机酒农最根本的区别,或许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对霜霉病(mildiou)的治理方法上。“无药不毒”乃是大自然之法则。抗争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将无酒可酿。而每种抗争方式都各有各的副作用,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使用有机契约所允许的硫酸铜,还是放弃“有机”使用合成杀菌剂(synthetic fungicides)?硫酸铜有剧毒,且很难化解,会慢慢在土壤中累积。从长远看,我认为使用硫酸铜的恶果将大于化学杀菌剂。“有机”是种标签,推行一整套行为标准,它迫使你做出死板,甚至夸张可笑的决定。

“我同有机酒农最根本的区别,或许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对霜霉病(mildiou)的治理方法上。。。从长远看,我认为使用硫酸铜的恶果将大于化学杀菌剂”
Mei: 回到种植方面的重要举措,除了上面提到的土壤维护,还有其他哪些呢?
JFM: 种植方面另一重要改变,是在2005以后逐步采用一种特殊的剪枝(Taille)方式。30年以下的“年轻”葡萄藤全部改用Cordon de Royat。老藤还是用Guyot剪枝法,但同过去只留4到6个芽眼的做法不同,我们决定保留10至12个芽眼的长枝条。每年到了四月下旬,则进行抹芽工作,去除一半贅芽,使得剩下的枝梢拥有更宽松的空间,更有效的利用光照。
Mei: 这样做之后的收益是否很明显?
JFM: 我观测到,在过去十年中我家葡萄的成熟期提前,葡萄树具备更强悍的抗白粉病和灰霉病能力。这种剪枝方式的缺点是技术要求高,费钱费时费力。如果处理不当,抹芽工作未在短时间内完成,贅芽将发展成幼梢,去除将对葡萄树带来伤害,使之疲惫。
长枝修剪法是Mugnier葡萄园中的“秘密”之一
Mei: 酒庄是否施行摘叶(éffeuillage)及绿色收割呢?
JFM: 很少去叶,主要是在花季开始前一段时间有选择性的摘除一些重叠的叶子,主要目的是预防白粉病。我庄最后一次绿色收割是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天然产量都极为低下,老天替我们完成了绿色收割。历史上曾出现过既产量丰沛又高质的年份,例如1999和2009。遗憾的是过去几年-2015年份除外-出产高品质的葡萄酒都必须以牺牲产量作为代价,别无选择。

Mei: 让我们来谈谈采收时机的问题。在Chambolle-Musigny村内,即便顶级酒庄之间,采收日亦会相差甚远。例如,Domaine du Comte de Vogue总是村里最早采收的,贵庄有时在其之后一周才开始。您到底是怎样决定采收日的呢?
JFM: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酒庄葡萄园的状况。即便同一产区,各家葡萄树状态的不同就必然导致采收时机的不同。在90年代,我家往往是村内最晚采收的酒庄,但在过去几年中却成了偏早采收的酒庄之一。这同我们的葡萄成熟期加快和提前有很大关系,我本人的决策原则其实并未有太多改变。对于黑皮诺而言,葡萄皮的酚类物质成熟度是我决定采收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只能通过亲自品尝葡萄提样来完成。我会咀嚼葡萄皮:一开始它是青涩无味的,单宁突兀干苦;慢慢的,葡萄皮中单宁会变圆润且富有香气。有些年份,即便潜在酒精度已经颇高,酸度下滑,还是必须耐心等待酚类物质充分成熟才能采摘。
各酒庄葡萄园状况之不同是导致其采收时机有差异的重要原因
Mei: 如果酒精度过高酸度下滑,您难道没有过熟的担忧吗?
JFM: 我丝毫不担心酒精度过高的问题,有些年份如2009年,我们有些酒款的酒精度超过14%,在2015年份,特级园的酒精度也都接近这个水平。
陈酿篇
Mei: 现在能否较详细的聊一下您陈酿方面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从采收开始。贵庄拒绝使用筛选台,这是为什么呢?
JFM: 所有的筛选工作都在田间完成,这是最有效也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我们采收季50个员工中45个在葡萄园采收,只有5个留在酒庄。筛选台对于排除不成熟的小个青涩颗粒有效,但对于勃艮第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灰霉菌。如果腐烂受损颗粒不在葡萄园中及时剔除,所渗出的带菌汁液在运输中将很快感染其它葡萄。我个人痛恨筛选台的工作方式。葡萄园中的筛选是种自然明智的工作,聚光灯下的筛选台却更像是个工厂,是可恶愚蠢低效的。我庄具备一个震动台,足已起到自动甩除水滴,昆虫和小颗粒未熟葡萄的作用。我们给予采收工足够的时间认真有效的完成他们的工作,人工筛选台在我看来是多余的。
如果腐烂受损颗粒不在葡萄园中及时剔除,所渗出的带菌汁液在运输中将很快感染其它葡萄
Mei: 贵庄的葡萄都是100%去梗发酵的,您从未尝试过带梗酿造吗?
JFM: 我确实尝试过!事实上,我庄1985至1993年份出品的酒都或多或少带梗。但在品尝比较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这种做法。我发现,全梗酿造的酒陈年后确实相当复杂诱人,但在年轻时却略带青涩之气,缺乏果味和圆润的口感,往往显得单薄冷峻。去梗之后,这些缺陷明显得到修正,并且我相信陈年潜力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全梗酿造的酒陈年后确实相当复杂诱人,但在年轻时却略带青涩之气,缺乏果味和圆润的口感,往往显得单薄冷峻
Mei: 您使用发酵前冷浸泡萃取吗?
JFM: 如果采收期间天气过热,我会将葡萄温度降到14-15度,但并不人为维持低温以延缓发酵,所以应该说,我并不施行所谓的“冷浸泡”。我同时使用不锈钢和橡木桶两种不同容器:木桶中的葡萄2-3天后发酵就自然开始,不锈钢中的则通常需要一周的时间。通过柔缓的去梗动作,我们尽量保持葡萄颗粒的完整无缺,这对放慢和拉长发酵过程以及萃取皮中复杂精致的香气至关重要。也正因此,我发酵期间几乎从不踩皮(pigeage),萃取是通过偶尔淋皮(remontage)非常柔和的进行。
通过柔缓的去梗动作,我们尽量保持葡萄颗粒的完整无缺,这对放慢和拉长发酵过程以及萃取皮中复杂精致的香气至关重要
Mei: 那您是在什么时刻开始踩皮动作呢?您是否对发酵施行温度控制?
JFM: 我对温度是控制的,但发酵期间温度上升的相当缓慢。整个浸皮发酵(cuvaison)持续长达18-20天,温度却到最后才抵达顶峰-可以高达38-40摄氏度。此刻,果汁中糖份已基本全部转换成酒精,最后的踩皮动作将促使葡萄颗粒中尚存的糖分最后释放,从而延长发酵时间。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持续一周之长。之后我们会榨汁,自然澄清24小时后入桶。自流汁(vin de goutte)和压榨汁(vin de presse)分开陈年,但后者最终往往还是混入前者。

Mei: 您在添加二氧化硫上的做法是怎样的?
JFM: 我对二氧化硫的添加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的最低量。通常仅在酒精发酵开始前和乳酸菌发酵完成之后极少量添加。除此之外整个漫长的18-20个月的木桶醇化期间,我基本上不添加一点二氧化硫。
Mei: 你是否通过装瓶时注入少量二氧化碳以弥补二氧化硫之低含量,增进酒的抗氧能力?
JFM: 二氧化碳是不能取代二氧化硫功能的。况且,二氧化碳含量必须保持在品鉴无法感知的限度以内,也就是每升600mg以下。我庄二氧化碳的含量通常在每升350-550mg之间,而在酸度偏高的年份则会相应少加,因为二氧化碳有锐化酸度的作用。
我对二氧化硫的添加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的最低量
Mei: 您对时下流行的“自然酒”(Mei注:完全不添加二氧化硫的酒)怎么看?
JFM: 我并不在意尝试这些酒。上次我喝了一款2008年份的“自然酒”,感觉像1959年份的。“自然酒”中酿酒技法的痕迹通常覆盖了风土的表达。几乎所有的“自然酒”都具有同样的,陈酿技法所带来的香气,人们很难分辨出它的风土来源。我觉得作为酒农,我们必须对最终消费者负责,而不应仅仅为了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哲学理念而酿酒。
“自然酒”中酿酒技法的痕迹通常
覆盖了风土的表达

Mei: 酒庄现在用新桶的比例是多少?对橡木的出处是否有特殊要求?
JFM: 不论年份产区,都在15-20%左右。我们同François Frères以及Remond橡木厂合作。我们当然选用最优质的橡木桶。但介于我们新木比例之低,橡木的特性对酒的品质及风格影响极小。
Mei: 贵庄的酒是否出现过瓶塞污染(TCA)的问题?您是如何控制木塞的品质的?
JFM: 我们在2004后替换了木塞供应商,并始终保持与三个不同供应商同时合作。首先,我们对生产商施加了一套严格的规格流程章法。到货之后,我们会首先在实验室中进行TCA含量测试。之后,进行第二道测试:将任选的100个瓶塞在纯净水中浸泡24小时,之后品尝木塞浸泡过的水。这道测试旨在检测木塞中除了TCA之外的其他异味,例如霉味等。目前我庄的木塞感染率一般控制在1%以下。
Mei: 那些不幸遇到1%TCA污染的客户是否能将酒退回呢?
JFM: 客户可以将瓶塞寄回酒庄,我们会对之进行实验室测试。如果经鉴定确实瓶塞污染,我们会提供替换服务。

Mei: 酒庄是否有考虑使用防伪设计?
JFM: 康帝庄庄主Aubert de Villaine曾同我商讨过共同协调抗伪的计划。我个人对此不是太感兴趣。我不想把我家的酒标设计成类似银行钞票。伪造品的存在正好提醒收藏家,让他们意识到从官方渠道购买葡萄酒的重要性。否则后果自负。
Mei: 很多收藏家朋友询问,酒庄的Clos de la Maréchale为何酒标上没有注明Monopole?
JFM: 对我而言,Monopole (独占园)同品质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我不觉得有把它印在酒标上的必要。其实,如果您注意酒标上最下面一行小字:“Seul Propriétaire au Chateau de Chambolle-Musigny”- 已经注明独占园性质。
Mei: 在我们过去的交谈中您曾提过,陈酿方面,你对所有葡萄园都一视同仁。不论出处,都以同样的方式发酵和醇化,您这样做背后的逻辑和理念是什么呢?
JFM: 是的,为了最大程度上透明地表达风土特征,我对所有产区都严格采用完全一致的方式陈酿,包括浸皮的时间,萃取之强弱,发酵温度,新木桶比例,装瓶时间等等,手法上都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信奉风土至上的理念,就不应该人为的强迫一款酒同它的天然倾向背道而驰。我们不应力图矫正某片风土的特征,弥补它个性上所谓的不足。我认为只有在陈酿中秉持绝对中性的原则,方能凸显每片风土的本色。
“如果我们信奉风土至上的理念,就不应该人为的强迫一款酒同它的天然倾向背道而驰。我们不应力图矫正某片风土的特征,弥补它个性上所谓的不足”
Mei: 那对于不同年份呢?
JFM: 我绝不根据不同年份调整我的陈酿手段。每个年份都有它的独特性,这也正是它有趣之处。比如,有些年份颜色深邃,有些则非常浅,天然使成,何必强迫每个年份都给出同样的颜色?在我刚接手酒庄时,曾经试图根据风土和年份调整技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例如,在寒冷的年份,成熟度偏低,单宁少颜色淡。你会说,这样的年份需要更多的人工介入,更强劲的萃取,方能弥补年份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你亦可理论,寒冷年份的单宁偏于青涩干苦,必须格外柔和萃取方可避免不熟的单宁渗入酒汁。又如,在新桶比例上,你会说,村级的酒缺乏天然的单宁,多些新木桶正好可以增强其结构感,而特级园本来就富含包括单宁在内的天然多酚物质,故而不需太多的新木桶带来更多的单宁;然而,反向推理也是可行的:村级酒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内涵和力度,故而木桶使用必须含蓄以免盖过酒本身的个性表达,而强大的特级园则能承受更高比例的新木桶。一开始,我陷入矛盾中,就决定不分风土年份一律以同样方式酿造陈年。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哲学。

Mei: 是否可以说,您对大自然是完全信赖的?
JFM: 是的,在陈酿上,我并不给风土和年份划分高低等级:对于每片风土,每个年份,我们必须尊重它特有的和谐。这些年,我愈发深信,大自然有着她自身的和谐。如果我们试图扭曲她,那么,我们做的越多,破坏天然和谐的风险就越大。你无法在酿酒房内重建平衡:现代陈酿技术无法将原先不平衡的变得平衡。大自然本身的和谐有时是人类知识无法充分解释的。在无知中我们必须承认,自然总是最完美的。
“大自然有着她自身的和谐。。你无法在酿酒房内重建平衡-现代陈酿技术无法将原先不平衡的变得平衡”
Mei: 聊到年份问题,最让您倾心的是那个年份?
JFM: 我不在意告诉你,但我的回答很可能造成误导。因为我是从酿酒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这同爱好者收藏家的角度可能很不同。对我而言,我最爱的年份往往是那些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最令我骄傲的年份。这往往是一些带来惊喜结果的艰难年份。
Mei: 例如?
JFM: 例如2013就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我31年的酿酒生涯里,几乎从未经历过老一辈人所描述的像60,7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年份。2013年,我曾一度对自己说,或许,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份。然而,结果却充满惊喜。2013年份丰满深邃,它的圆润肥厚对于这样一个寒冷艰难的年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刚入桶不久,它的酸度似乎有些突出,现在却完美无痕的融入酒体。或许2013并非易饮诱人,讨喜大众的年份,但却个性鲜明,并具备在我看来比2012和2014都更强的陈年潜力。当然这些都是就我们庄的酒而言。
“2013年份丰满深邃。。。具备比2012和2014都更强的陈年潜力”
Mei: 除了2013,还有那些年份给您带来了惊喜?
JFM: 2010,2008,2004都是这样的年份。2010现已成为公认的杰出年份,但在采收的时刻,对于这个年份的潜质却众说纷纭。2004对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一年,我们收回了Clos de la Maréchale, 酒庄的产量翻了3倍多。我雇佣了新的7人团队,扩建了酒窖(拥有四层场地空间),添加了新的酿酒设备。2004是个极为艰难的年份,葡萄园间的工作充满挑战。
Mei: 不少人认为2004年份特有的青涩气息同那年有很多瓢虫有关。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JFM: 2004年份确实有很多瓢虫,需要在筛选时剔除。但这仅仅是因素之一。很多青涩其实同葡萄成熟度欠缺有关。这个年份的单产量必须控制在很低,否则绝对产不出好酒。Clos de la Maréchale在2004年经历了绿色收割,一半以上的葡萄被去除!2004成为令我自豪的高品质年份。
2004年份的很多青涩其实同葡萄成熟度欠缺有关。这个年份的单产量必须控制在很低,否则绝对产不出好酒

Mei: 媒体对于创造“伟大”年份也功不可没,例如最新的2015年份。您对这个年份怎么看?
JFM: 2015是一个极其极其伟大的年份(降低音量)。但我们对此不应该过多宣扬!
Mei: 2015年份是否有酸度偏低的担忧?
JFM: 现在下定论或许过早,但我对2015黑皮诺缺乏酸度的说法不敢苟同。确实,采收来的葡萄总酸度偏低,但其中苹果酸的比例和钾(发酵期间会中合葡萄汁和酒汁中的酸)的含量都非常低 - 这意味着2015将是个酸度非常稳定的年份。
Mei: 许多收藏家会关心贵庄的酒何时能进入适饮期?
JFM: 我们庄的酒,一个“小年”的村级陈年潜力是10到20年;如果是杰出年份,则需40-50年方可抵达巅峰。例如Chambolle-Musigny Village 1990年份现在仍很年轻,远未达到它的顶峰。而对于一级园和特级园,陈年潜力几乎是无限的。
一个“小年”的村级陈年潜力是10到20年;如果是杰出年份,则需40-50年方可抵达巅峰
Mei: 这么说,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享受到鼎盛时期的杰出年份和杰出风土? 像2005这样昂贵的年份,或许需要很久方能打开。。。
JFM: 我总是同客户强调,伟大年份和伟大的酒从来都不是愉悦感的同义词。一款酒之伟大存在于它仍未兑现的未来,而非衡量今日享受之尺度。此刻能给我们带来最大乐趣的往往并非这些酒。作为收藏家,只购买所谓的伟大年份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伟大年份和伟大的酒
从来都不是愉悦感的同义词“
Mei: 从酿酒技术的角度和哲学角度,请问您对一款伟大的酒的定义是什么?
JFM: 从技术角度,一款伟大的酒的真正标志是其回甘长度(longueur),因为这是据我所知唯一无法用现代技术手段在酿酒房中创造出来的“优点”。其他因素,例如,酸度,甜度,香气,木桶,浓郁度等等,都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来调整甚至伪装。从哲学角度,一款伟大的酒之真髓隐藏于它此刻尚未呈现的那部分。你手中这杯年轻的酒,你现在所能感受到的它的一切,往往仅是其全部内涵的冰山一角,它的秘密存在于其演变中无法揣测的未来。一款伟大的酒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慢慢揭示其神秘的面纱下的真实面容。
从技术角度,一款伟大的酒的真正标志是其回甘长度(longueur);从哲学角度,一款伟大的酒之真髓隐藏于它此刻尚未呈现的那部分。
![]()

更 多 文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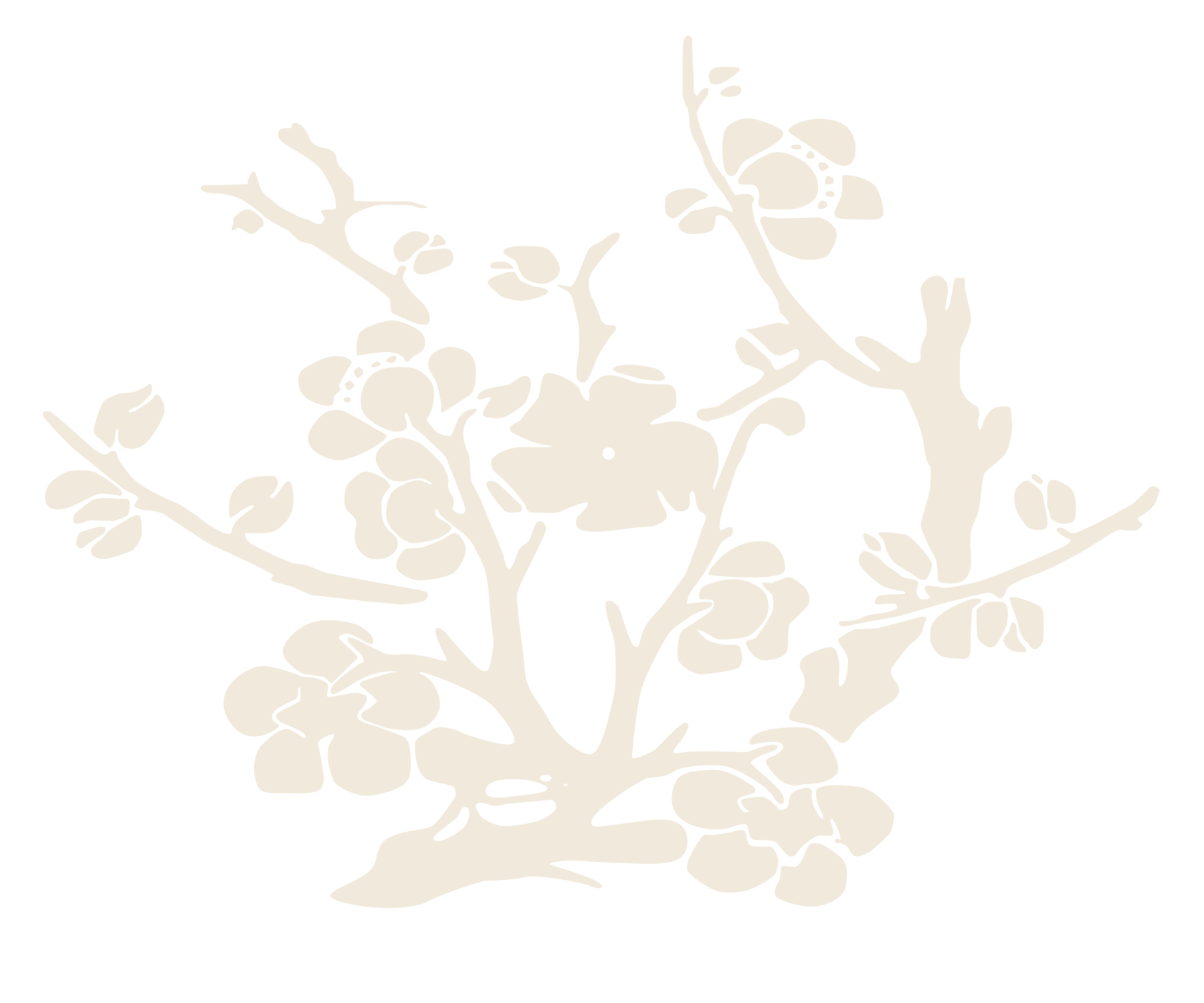
梅 专 栏
5 Place de L'Europe, 21630 Pommard, Côte d'Or, France
contact@mhclimatsselections.com
5 Place de L'Europe, 21630 Pommard, Côte d'Or, France
contact@mhclimatsselections.com
本网站所有照片,除非特别标注,皆由 Mei Hong 本人拍摄。版权归属作者,未经允许请勿转发。
© E.U.R.L MH Climats Sélections![]()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8535号 沪ICP备2020026059号-1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8535号 沪ICP备2020026059号-1






































